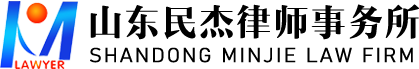《中国检察官》2025年第12期刊载了《“接私活”型职务侵占行为的刑法定性》一文,该文通过实务案例认为,主营业务对价属于本单位财物,行为人滥用内部管理职权,通过调用内部人财物私自承接新业务,将新业务对价占为己有的,构成职务侵占罪。我们认为,对此类案件是否足以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还是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定性为宜,存在商榷空间。
【基本案情】
论者据以展开讨论的案件基本信息是:2020年,某公司项目经理Z某某利用管理某环卫保洁项目的职务便利,与项目主管R某某合谋,在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由R某某以某公司名义向该项目合同外部分集贸市场、商铺等经营场所收费,安排下属环卫工人使用某公司设备对收费的经营场所进行保洁和垃圾清运,所得收益由R某某分配给Z某某和下属环卫工人。2021年6月,M某某接替Z某某担任项目经理,继续伙同R某某继续以上述手段收费获利。
【争议焦点】
在上述案情中,R某某、Z某某、M某某三人利用职务便利接私活,并使用本公司的人员、设备完成私活并以此牟利,具有刑事可罚性,应予否定评价。主要分歧在于,R某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
【法理分析】
论者认为,R某某等人私分的合同外收入系商户购买保洁和垃圾清运服务的对价,上述服务由R某某等人组织环卫人员和设备提供,R某某等人、环卫工人、设备均属于某公司,故R某某私分的合同外收入系是本单位的确定收益,R某某等人因此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述论证整体思路正确,即要认定R某某等人构成职务侵占罪,需以论证其私分的合同外商户支付的对价是所在单位的财物为前提。但我们认为,该前提是否能够成立存在较大疑问。具体如下:
首先,论者以行为人使用本单位人力和设备为由认定该部分服务收入应归单位,理据不足。本案中,合同外商户的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虽系R某某等人安排本单位下属环卫工人使用本单位设备完成,但单位人力资源+单位设备≠单位收入,以单位人员与单位设备的简单叠加等于单位收入的逻辑过于粗糙,不能成立。R某某等人取得商户支付的保洁和垃圾清运对价,除需要投入人力和设备之外,还需要先期与该合同外的商户进行接触、磋商、洽谈;在安排下属环卫工人开展合同外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环节中,进行管理和统筹,并在正常工资收入之外,向环卫工人支付额外的报酬(基本案情中亦提到,R某某从合同外商户处获利后,除与Z某某和M某某分配外,还向下属环卫人员进行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在合同外商户不具有善意或者未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R某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则其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需自行承担,故R某某等人还要因此承担相应的履约风险。因此,论者忽视R某某等人接触与洽谈商户、对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及下属环卫人员的统筹与管理、市场风险的承担等要素的价值,忽视R某某等人及同样获得分配的环卫工人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付出,将R某某等人使用本公司人员和设备直接等同于本公司应获得商户支付的对价,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R某某等人成立职务侵占罪,存在逻辑上的缺失与跳跃。
其次,行为人违背忠实义务,侵占公司商业机会,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上,从现行规范的视角来看,R某某的行为虽因上述原因未必构成职务侵占罪,但其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占所在公司的商业机会,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所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本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二)》(2024年3月1日施行)修订,已将犯罪场景由国有公司、企业扩展至民营经济主体。修订后本罪的存在,也能够有效解决实践中具有刑罚必要但距离职务侵占罪尚有一定距离的案件定性问题。当然,与典型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犯罪相比,本案中R某某等人的行为还利用了所在公司的人员和设备,从这一角度而言,R某某等人的行为实际上是未达到职务侵占的程度,但超出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范畴,介乎二者之间。对此,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在不考虑溯及力问题的基础上,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定性更为适宜。
最后,合同外商户支付的对价虽不宜评价为本单位财物,但行为人仍可在特定情形下构成对部分财物的职务侵占。R某某等人在履行自己与商户的事实合同过程中,如不仅使用本公司人员和设备,还利用职务便利使公司承担本应由R某某等人支付的款项,对该部分事实可认定为职务侵占。例如,R某某等人安排下属环卫人员向合同外商户提供保洁和垃圾清运服务时,因该部分服务与所在公司无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油费等交通费用不应由公司承担,而应由R某某等人自行负担。但如R某某等人通过报销等方式,使所在公司承担了该部分费用,显然属于“花公司的钱,办自己的事”,在达到证据标准和追诉起点的情况下,对该部分行为及数额可认定为职务侵占罪。